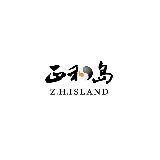當(dāng)今社會(huì),未來變得不可預(yù)測(cè),充滿了不確定性。好像生活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意義感。
再加上社交媒體的放大,“上個(gè)10分鐘的網(wǎng),給自己確診一身‘病’”,我們很容易感到焦慮、自卑、不安全感、不確定感、無意義感,等等。
這些不僅是個(gè)人面對(duì)的痛苦,也是這個(gè)時(shí)代的特點(diǎn)。韓炳哲在《妥協(xié)社會(huì)》一書中提出,“我們生活在一個(gè)試圖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會(huì)”。在積極主義的影響下,我們似乎失去了表達(dá)自我悲傷的權(quán)利,變得更加敏感、焦慮。
面對(duì)不確定的未來,我們應(yīng)該做什么?如何做?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尋求一些確定?
在劉擎和嚴(yán)飛的新書《世界作為參考答案》中,他們對(duì)于上述問題作了深度探討,以下是他們對(duì)于這些問題的思考,希望對(duì)你有所啟發(fā)。
編 輯:米麗萍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本文摘編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劉擎 嚴(yán)飛著《世界作為參考答案》一書。
一、功績(jī)社會(huì),我們沒有權(quán)利表達(dá)痛苦
現(xiàn)代社會(huì),痛因越來越少,痛感越來越強(qiáng)。似乎有一種隨處可見的“痛苦恐懼癥”。
在自媒體平臺(tái)上,我們經(jīng)常看到諸如“10個(gè)技巧幫你擺脫焦慮”的文章,這類內(nèi)容往往點(diǎn)擊率極高,大家都在追求用一些方法和捷徑迅速地?cái)[脫痛苦。
人們似乎對(duì)任何形式的痛苦都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不愿意去面對(duì)愛情的痛苦。但是另一方面,每個(gè)人內(nèi)心深處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痛苦的東西想要表達(dá)出來,又害怕去表達(dá),從而陷入了一種矛盾的狀態(tài)之中。
然而,放大到社會(huì)層面,由于人與人之間深度連接,形成了復(fù)雜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當(dāng)一個(gè)人感到痛苦的時(shí)候,也許他可以選擇自我療愈,但是當(dāng)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相類似的痛苦的時(shí)候,個(gè)體的痛苦就變成了時(shí)代的痛苦。
痛苦的內(nèi)容也有很多:焦慮、自卑、不安全感、不確定感、無意義感,等等,并且這種痛苦有可能跨代傳遞。
韓炳哲在《妥協(xié)社會(huì)》一書中提出,“我們生活在一個(gè)試圖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會(huì)”。
今天的社會(huì),大家都懼怕否定性,不喜歡消極,重視積極的、肯定性。人們似乎失去了表達(dá)自我悲傷的權(quán)利,甚至對(duì)痛苦的表達(dá)成了一種社會(huì)忌諱,企圖把人們塑造成對(duì)痛苦極不敏感的,永遠(yuǎn)感到積極、幸福的功績(jī)主體。
當(dāng)下一些微信公眾號(hào)有一個(gè)叫做“夜讀”或者“夜話”的欄目,固定在每天晚上10點(diǎn)推出。這些欄目像“打雞血”一樣推送很多“心靈雞湯”的小文章,不停地強(qiáng)調(diào)你要勤奮與樂觀,強(qiáng)調(diào)必須看到人生的光明面。
但是想象一下,“996”的你下班回到家,勞累工作了一天想躺在沙發(fā)上休息,或者今天工作上有不順心的事情,想痛罵一下不人道的公司制度,發(fā)泄自己的情緒。
這時(shí)候10點(diǎn)整的心靈雞湯來了,說你要積極樂觀、美好地看待每一天,你要正能量——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想正能量,我想稍微給自己一點(diǎn)放松;我今天非常沮喪,心情不好,我想和閨蜜、好友傾訴一下,想自己一個(gè)人待著。
這些心靈雞湯,仿佛在否認(rèn)和抹去人們的痛苦和不滿——我們今天不允許大家表達(dá)一些不積極的,甚至是悲觀的、消極的東西,不允許大家反問、反思說我確實(shí)感覺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我承認(rèn)自己做的是沒有意義的工作不行嗎?不可以嗎?對(duì)不起,還真不可以。你必須保持樂觀的態(tài)度,繼續(xù)投入到積極的工作當(dāng)中去。如果你敢于表達(dá)自己的痛苦,就可能被視為不符合社會(huì)主流。
這種趨勢(shì)讓我越來越擔(dān)心,當(dāng)今的年輕人連表達(dá)悲傷和焦慮的權(quán)利都逐漸喪失了,這對(duì)他們的人生又意味著什么呢?
我們?nèi)绻肋h(yuǎn)點(diǎn)贊積極正能量,痛苦就會(huì)消失嗎?積極主義看上去是在給予我們心靈的慰藉,其實(shí)恰恰相反,年輕人應(yīng)該擁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權(quán)。
這種自主選擇不一定總是有明確的意義,但可以提供一種松弛的狀態(tài)。松弛不是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松散形態(tài),而是說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一個(gè)邊界里掌握自己的人生。當(dāng)人們能夠主宰自己的生活,即使工作再忙碌和辛苦,也能感受到一種內(nèi)在的成就感。
二、直面痛苦,才能治愈
痛苦對(duì)人生的體驗(yàn)和意義是多樣的,對(duì)待痛苦的方式也是如此。但有些應(yīng)對(duì)痛苦的方式不太可取,比如完全沉湎于痛苦,或者徹底回避痛苦,我們還可以探索更可取的應(yīng)對(duì)方式。
就我自己而言,面對(duì)精神層面的痛苦是通過寫作。我們那一代有許多人有寫信和寫日記的習(xí)慣。
在我看來,失敗感可能是痛苦的一個(gè)重要來源,我自己的感覺是如此。無論是你想要成就的一項(xiàng)事業(yè)的目標(biāo),還是你在感情上寄托愛戀的一個(gè)人,如果你付諸了巨大的努力,那些深切和強(qiáng)烈的愿望還是沒有達(dá)成,就會(huì)在精神上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失敗感。
那么這種失敗感我是怎么應(yīng)對(duì)的呢?一開始也是挺幼稚的,就是啟動(dòng)一種防御機(jī)制“否認(rèn)”,說這件事情對(duì)我不重要,沒有達(dá)成也沒關(guān)系,這樣就否認(rèn)了失敗。
但是人真的能逃過自己?jiǎn)幔糠凑也恍小t斞傅摹秱拧分心兄魅斯干傆X得背后有另外一個(gè)聲音,其實(shí)那是自己的一個(gè)聲音。
我無法躲避這種聲音,我能治愈的失敗感都是以極端的方式直面自己,就是把失敗的經(jīng)歷一步步拆解開來,鉆到所有的細(xì)節(jié)里,甚至可以說是對(duì)自我剖析有點(diǎn)沉湎,為的是辨析哪些會(huì)令自己緊張和恐慌,哪些可能會(huì)感到羞恥或憤怒,然后把這些最有痛感的細(xì)節(jié)反復(fù)揉碎和咀嚼,直到我有能力從容,能將這些細(xì)節(jié)放置到整體的自我敘事中,這時(shí)候我就覺得自己能超脫失敗的痛苦。
這種過程時(shí)常帶著強(qiáng)烈的情緒,是自虐的。因?yàn)槟忝髅鹘?jīng)過了一場(chǎng)失敗,但你還要反復(fù)細(xì)致地重溫那些失敗的痛楚。我對(duì)痛苦的治愈過程,幾乎總是經(jīng)由更痛才可以走向解脫。
我想,肯定有人比較“心大”,更容易就能超脫了。年紀(jì)大了可能也容易些,但在少年時(shí)代,因?yàn)橐淮慰荚嚮蛘呤裁幢荣惖某煽?jī)不夠理想,就會(huì)特別和自己較勁。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種方式很耗能,如果能有一點(diǎn)“得過且過”也可以。
孔子講中庸之道,亞里士多德講中道原則,這些道理很早就會(huì)背誦,但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內(nèi)仍然不是自己的道理。
我是通過很多痛苦的歷練之后才慢慢明白,什么樣的事情要投入多大的精神、情感和智識(shí)的精力才是恰當(dāng)?shù)摹?/strong>分寸感和比例原則都是很重要的,但在這方面我其實(shí)很晚熟。
三、去做喜歡和值得做的事
當(dāng)下的境況有很多變數(shù),有不確定性,原有的預(yù)期可能會(huì)落空。前幾年考上大學(xué)的年輕人,有些能進(jìn)“985”或“211”這類學(xué)校,本來指望會(huì)有一個(gè)好的工作,這是合理的期待。
但當(dāng)這個(gè)前景不那么明朗的時(shí)候,好像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意義感。但是讓我們想一想,如果本來就沒有這樣一個(gè)可期待的前景,你又應(yīng)該做什么?
想想“50后”與“60后”那一代人,在歷史條件的約束下,在整個(gè)群體沒有多少選擇的境遇中,仍然有不少人沒有虛度年華,他們是怎么做到的?
讀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對(duì)我最大的啟發(fā)是,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以及人對(duì)自由的向往,這些不僅是值得追求的價(jià)值,而且是在每個(gè)年代里都值得爭(zhēng)取的目標(biāo)。
茨威格相信,無論在什么年代,文化上的探索、人類和平與人道主義都是值得奮斗的目標(biāo)。“二戰(zhàn)”爆發(fā)前夕他在英國(guó),從倫敦搬到偏遠(yuǎn)的小地方去,專注于寫作兩卷本的巴爾扎克傳記(《巴爾扎克傳》)。
他認(rèn)為,這就是我本來應(yīng)該做的事情,哪怕現(xiàn)在英國(guó)宣戰(zhàn)了,我還是應(yīng)該做這件事情。
所以,即便處在困境甚至絕境之中,即便在前景不明、方向未定的時(shí)候,最能賦予你強(qiáng)健生命力的方式,就是選擇去做那些在所有年代、在所有歷史條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
比如鍛煉身體;比如閱讀、寫作和思考,關(guān)心公共事務(wù),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比如像匠人一樣耐心磨煉一種技藝,日臻完善;比如去外地旅行,看大千世界;比如認(rèn)真與人交往,尋求知己,體會(huì)深情厚……
所有這些活動(dòng),不只讓自己能夠更好地應(yīng)對(duì)困境與劇變,而且這些活動(dòng)和體驗(yàn)本身就是好的,實(shí)現(xiàn)了生命的內(nèi)在價(jià)值。這也正是茨威格終其一生所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去做自己喜歡與值得做的事情就好。如果你有某種技藝,比如喜歡做家具,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歡閱讀,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歡唱歌、跳舞,你有才藝,愿意做短視頻,這本身就是好的。
說不定哪一天這些活動(dòng)會(huì)給你帶來實(shí)際的回報(bào),但是即便沒有實(shí)際的回報(bào),這本身就有價(jià)值,不僅讓你快樂,而且會(huì)讓你獲得對(duì)自己的肯認(rèn),賦予生命的意義感和價(jià)值感。
當(dāng)然,價(jià)值感最好是說我把這個(gè)事情做了,同時(shí)帶給我一筆收入。錢很重要,但金錢不是一個(gè)非常可靠的意義來源。
你可以和周圍的小伙伴們一起去做自己認(rèn)為值得做的事情,哪怕一起打游戲,也能夠體驗(yàn)到自身的活力、智性和熱情,這些就是好的事情。
在任何處境下,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唯一能夠拯救我們意義匱乏的方式就是,做那些在所有境遇中,在所有時(shí)代都值得做的事情,你堅(jiān)持做下去,未必能夠給你實(shí)惠的金錢或物質(zhì)的回報(bào),但它能在精神意義上鼓舞你,成為一個(gè)更豐沛的生命。
四、重建自我,重建連接
德國(guó)哲學(xué)家斯文婭·弗拉斯珀勒在《敏感與自我》里提出,我們今天的社會(huì)是一個(gè)高度敏感性的社會(huì),在敏感性社會(huì)里,每個(gè)個(gè)體無論是心理層面還是道德層面都變得更加敏感,比如對(duì)貧富差距的敏感、對(duì)性別議題的敏感等。
今天的人會(huì)接收到來自不同維度的信號(hào),變得更加敏感,更容易陷入焦慮。人們面臨的信息爆炸和社會(huì)壓力是前所未有的。
比如,年輕人會(huì)不斷地將自己的和父母那一代的生活經(jīng)歷進(jìn)行對(duì)比,思考為什么在生活條件明顯改善的情況下,工作機(jī)會(huì)卻變得越來越少?他們也會(huì)與那些家庭條件更優(yōu)越的同齡人相比,質(zhì)疑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羅馬,但另一些人卻擁擠在通往羅馬的路上。
這種持續(xù)的比較和競(jìng)爭(zhēng)感,不僅來源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直接觀察,還被社交媒體所放大。年輕人每天都在滑動(dòng)手機(jī)屏幕,看到的都是別人精心策劃的生活片段,這種視覺和心理的沖擊使他們對(duì)自己的現(xiàn)狀感到不滿和焦慮。
未來怎么辦?既然卷不動(dòng)也躺不平,只能成為45度斜桿青年,在躺平和振作之間反復(fù)尋求平衡。
但敏感性帶來兩個(gè)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我們對(duì)人類的疾苦,包括對(duì)他人和自己的疾苦有更加強(qiáng)烈的反應(yīng);但另一方面也會(huì)帶來脆弱,因?yàn)槟忝舾辛耍銜?huì)脆弱。所以有位日本學(xué)者寫了本書提倡“鈍感力”。
但鈍感不是麻木,敏感和鈍感是可以共存的。其實(shí)我們知道,面對(duì)生活的各種困境,既需要敏感,也需要在敏感之后有很強(qiáng)的理性來分析和澄清,你能夠舍棄什么,什么是對(duì)你最重要的,才能幫助你做出選擇。
人是通過自己的遭遇和敘事來建構(gòu)自我的,自己的故事發(fā)展和改變,就是自我重構(gòu)的過程。在平穩(wěn)的時(shí)代,每個(gè)人的故事相對(duì)穩(wěn)定,自我重構(gòu)是緩慢的,也是相對(duì)順暢的。但在最近幾年,似乎每個(gè)人都急促地重新尋找自我,重新構(gòu)建自我。這種倉促造成某種茫然的困境。
應(yīng)對(duì)困境的關(guān)鍵,是要澄清自己:什么是我最根本的關(guān)切,什么是我最本真的意愿,這不只需要理性的反思,還和自己的感受息息相關(guān)。最終去發(fā)現(xiàn),對(duì)你來說最有價(jià)值的、值得做的,在所有的處境中值得追求和努力的事情。
我們不僅要重建自我,而且還要重建連接,建立人和人之間真實(shí)的連接。在數(shù)字時(shí)代,社交媒體、即時(shí)通信軟件已經(jīng)成為我們?nèi)穗H交往的路徑依賴,可是人和人之間的社會(huì)臨場(chǎng)感卻消失了。
當(dāng)每個(gè)人都變成了“符號(hào)”和“頭像”,我們就無法即時(shí)感知到人和人交往過程中具身的社交線索,遑論去捕捉到那些轉(zhuǎn)瞬即逝的情感流動(dòng)。
此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更加有必要去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間真實(shí)的連接。而這種連接的建立,最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就在于走出來,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很多新鮮有趣的活動(dòng),重新去制定一些游戲的規(guī)則。
在世界的浮沉中,我們或多或少都在尋找通向自己出口的道路。在這個(gè)過程中,盡管有著大大小小的困難,但我們應(yīng)該努力從更廣闊的維度來思考,向世界打開自己,看見多元生發(fā)的可能性。
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寫道:今天,我們心神不寧地懷著破碎了的心情,像個(gè)盲人在恐怖的深淵中四處摸索,我依然能從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這種繼承下來的信念,認(rèn)為這種倒退只是“前進(jìn)”過程中的一個(gè)間歇,以此來安慰自己。
五、且認(rèn)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
人總是向往自由、探索新的天地,想象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在別處的生活,不斷地變化,這好像是喜新厭舊。
但實(shí)際上,人類是“喜新戀舊”,因?yàn)槲覀円残枰枢l(xiāng)的那種親切和熟悉,那種確定性和歸屬感,讓我們能完全安心的地方,那就是家鄉(xiāng)。
但是,我們又不甘愿留守在家鄉(xiāng)安頓自己,總是想要出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所以才有了“故鄉(xiāng)”。
如果你不離開家鄉(xiāng),就沒有所謂故鄉(xiāng),故鄉(xiāng)是過去的家鄉(xiāng),有故鄉(xiāng)的人就已經(jīng)離開家鄉(xiāng)了。
“家”對(duì)于我們意味著什么?至少可以把它分解成兩重含義,一個(gè)是物理意義上的家,一個(gè)是精神意義上的家。
家最樸素的意義就是你熟悉、確定、可以信賴和依靠的處所。人在家里會(huì)有一種天然的自由,這是感到無拘無束的自在。
在精神意義上也是類似的,你使用你特定的語言,有時(shí)候可能是方言,是特別自在的,近旁的人都聽得明白,時(shí)而可能會(huì)心一笑。
可是,如果感到過于自在,可能會(huì)覺得乏味,沒有新鮮感,也就毫無挑戰(zhàn)性。所以你又會(huì)渴望自由,向往遠(yuǎn)方的新天地。
就像我們最初到外地上大學(xué),走進(jìn)新的校園,一方面是激動(dòng),一方面是不安,這種激動(dòng)而不安的感覺和我們“在家”的那種自在松弛的感覺很不一樣。所以現(xiàn)代人往往生活在這兩種欲望的張力之中。
究竟如何是好?這取決于每個(gè)人的個(gè)體狀態(tài),有的人慢慢適應(yīng)了,能夠在不斷變化的新穎探索中找到自己,安頓自己,而有的人始終會(huì)有不適感,就會(huì)有很深的鄉(xiāng)愁,不斷涌起回歸家園的渴望。
但麻煩的是,如果你真的回到故鄉(xiāng),可能會(huì)發(fā)現(xiàn)那個(gè)“家”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變,家鄉(xiāng)的景觀變了,人的觀念也變了,甚至面目全非。你會(huì)發(fā)現(xiàn)“故鄉(xiāng)不再是故鄉(xiāng)”,不再是那個(gè)讓你能熟悉自在的故鄉(xiāng)。于是就有了無處安放的鄉(xiāng)愁。
“鄉(xiāng)愁”最深刻的含義是一種“無根的漂泊感”,在根本上是精神意義上無處安頓自己的困惑。因此,簡(jiǎn)單地在地理意義上回到故鄉(xiāng),或者把過去的書信、日記和遺跡都找出來重構(gòu)自己失落的童年,并不一定就能找到生命意義的根基,從而在精神和情感上安頓自己。
在我看來,如果要應(yīng)對(duì)鄉(xiāng)愁中的那種消極、沮喪和迷茫的情緒,我們首先要打破一個(gè)迷思(myth),那就是存在一種永恒家園的意象,通過返回(物理意義的)家鄉(xiāng)獲得溫暖的、自在的、可完全信任的依賴,一種真正的歸屬感。
現(xiàn)代人必須有一種堅(jiān)韌無畏的勇敢來面對(duì)永恒的鄉(xiāng)愁,放棄那種幻想——存在一個(gè)對(duì)你永遠(yuǎn)敞開懷抱的故鄉(xiāng)。我們要尋求的那個(gè)真正能安頓自己精神的“故鄉(xiāng)”并不是現(xiàn)成的“在某處”,而是一個(gè)有待自己去造就的“精神家園”。
當(dāng)然,這種重建精神家園的努力,可能是終其一生的探索。在這個(gè)過程中,我們的故鄉(xiāng)可以成為一種精神資源。
陳寅恪1948年在廣州的時(shí)候?qū)懥艘皇自姡詈笠痪浣小扒艺J(rèn)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當(dāng)時(shí)他身逢亂世,在兵荒馬亂的境遇中如何安頓?他就決意將此地當(dāng)作故鄉(xiāng)好了,這當(dāng)然是精神意義上的故鄉(xiāng)。
俗話說“三十而立”,立的不是金錢的飽滿,而是個(gè)人的精神世界,一個(gè)活在世界上感到意義的生活錨點(diǎn)。
要應(yīng)對(duì)那種懸浮的、無根的狀態(tài),就需要你在一個(gè)地方扎根,這不是說一輩子也不離開某個(gè)地方。而是說無論到哪里,都要與周遭的人與物發(fā)生深入一些的關(guān)聯(lián),否則就只是過客。
當(dāng)我們面對(duì)那種無根的漂泊感的時(shí)候,可能很容易失落,感到不知身處何處,好像是生活在“nowhere”,但像我一位朋友所說的,我們可以將“nowhere”這個(gè)詞拆解為“now here”,此刻就生活在這里。
也是朱光潛先生的六個(gè)字,“此身、此時(shí)、此地”。
排版| 椰子| 米禾輪值主編| 夏昆
特別聲明:以上內(nèi)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nèi))為自媒體平臺(tái)“網(wǎng)易號(hào)”用戶上傳并發(fā)布,本平臺(tái)僅提供信息存儲(chǔ)服務(wù)。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北京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