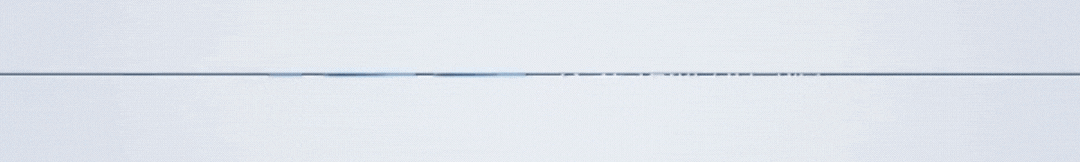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引言:
與大城市越來越來寡淡的年味形成鮮明對照,DeepSeek在近期火爆出圈,引發了各界人士的熱情關注。
不去探究復雜的技術問題,DeepSeek至少有兩點是外行普通人特別感興趣的,一是堅持自主研發,通過與國際科技產業前沿的對話,形成自主的技術路線和科研組織模式,二是堅持開源技術路線,通過多原理和技術集成,實現了相比于許多閉源大模型的成本優勢,這就能在較短時間內建立了龐大的用戶群。
這兩點之所以特別吸引人,是因為在長期的大國科技競爭中,人們習慣了從科技的先進性以及先進部門的規模和實力等角度來看待“科技進步”,而DeepSeek同時推進自主和開源,使大家意識到,比起僅關注“先進性”而言,“自主做出能廣泛使用的先進產品”毫無疑問是更重要的。
國際關系學者Jeffrey Ding在2024年出版了新著《科技與大國崛起》(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用“通用性技術擴散理論”挑戰國際關系學界長期占主流地位的“先進部門理論視角”,指出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現在,能夠促進先進技術更廣泛擴散和應用的制度才是幫助一國崛起并成功超越原有大國的基礎條件。Ding在他的書里專門辟出一章論述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但是由于AI是一個仍處于不斷探索過程中的先進技術,作者并沒有梳理出針對當前狀況有啟發的創新形態或者制度機制。DeepSeek至少在這一方面展現出來令人振奮的亮點:借助開放的創新環境做出更有利于大眾使用的先進技術產品。這個實踐所蘊含的理論意義值得我們持續加以挖掘。
本期推送的文章,主要部分是我們在去年12月中旬完成的,在當時,人工智能前沿領域興起的挑戰Scaling Law的種種探索,還沒有吸引國內觀察者的廣泛注意。鄭永年教授在近期提出一個“中國能否成為開源國家”的問題,系統論述了加大開放力度對于中國的價值。我們將繼續沿著這個提示推進思考——對我們來說,密切關注國際科技和產業前沿,是為了更好構建對于中國與世界發展有益的創新環境。中國邁向“開源國家”(開放創新的國家),需要更多地與世界融為一體,也需要更多地激勵創新資源在國內不同人群、不同行業中的擴散。人工智能能否真正成為新一代通用性技術(GPT),還未有確定答案,但類似DeepSeek這樣在這個方向上的探索努力,是怎么強調也不為過的。
——蔣余浩(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
多個跡象表明,人工智能前沿領域正步入新一輪技術變革期:作為當前人工智能主流技術路線的大語言模型(LLM),在最近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在近期,國際科技產業界提出一系列技術變革的新探索和新理念 。人工智能前沿領域的開放性、創造性和活躍度,已經激發了全球資本、科研和產業各界的新一輪熱情。
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目前針對大模型而涌現的各種挑戰,非但不會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先位置造成威脅;相反,正是美國支持多樣探索的制度環境,使得科技產業界的持續創新只會不斷鞏固和加強美國的領先地位。
這種傾向在特朗普實施“新政”之后,會變得更加顯著。可以預見,特朗普的科技政策將是對內加強創新激勵,對外實施更嚴厲的封鎖和遏制,中國面對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總之,相比于關注具體的科技發展細節,中國更需要認真研究激勵前沿科技持續革新的制度條件。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指出中國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為“美國產業的警鐘”。圖源:新華社
一、人工智能主流技術路線面臨的困境
大語言模型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主流技術路線,這一技術路線于2022年底因ChatGPT的推出而到達高峰。但是,在近期,這個技術路線陷入明顯的發展困境。
(一)海量投入的邊際收益顯著下降,“Scaling Law”效力遭到一定質疑
“Scaling Law”是對過去數年以來大模型發展狀況的一種經驗性總結,指的是模型性能將伴隨網絡規模、訓練時間、語料數據、算力投入的增加而指數級增長。
在“Scaling Law”引導下,開發大模型的費用越來越高昂。斯坦福大學發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指出:2017年最初的Transformer模型訓練成本約為900美元;2019年發布的RoBERTa Large訓練成本約16萬美元;2023年OpenAI的GPT-4和谷歌的Gemini Ultra的訓練成本則分別達到了約7800萬美元和1.91億美元。據估算,在過去8年,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訓練成本每年增長2至3倍,這表明到2027年最大規模的模型訓練成本將超過10億美元。

不同AI模型的訓練成本和計算資源 消耗,訓練更大規模的模型需要巨大的計算資源。圖源:AI Index Report 2024 - Stanford University
但是,高投入已經越來越不能保證必然帶來高性能,“Scaling Law”的效力在近期遭遇質疑。2024年11月,一家有全球影響力的媒體機構發布詳細報道指出,OpenAI、Google、Anthropic這三家科技巨頭的大模型新產品并沒有達到研發預期:與此前幾代產品突飛猛進式的性能迭代相比,OpenAI新一代旗艦模型(內部定名為Orion)不能被認為實現了跨越式發展;Gemini和Opus3.5同樣遇到類似情況,突破性并不顯著。在近期,越來越多的技術先鋒、企業領袖和知名投資人,都開始公開質疑“Scaling Law”的有效性。

據外媒報道,OpenAI旗艦模型Orion改進速度顯著放緩,引發關于是否消耗更高的成本來訓練AI的討論。圖源:新華社
(二)大模型產業集中化程度嚴重,“公-私”結構失衡影響未來的創新
在“Scaling Law”的牽引作用下,巨量資源和資本流向少數科技巨頭,這造成了以這些科技巨頭為核心的產業界掌握過強的主導權。科技界權威雜志Science在2023年3月刊登過一篇文章,對當前人工智能領域的資源占用狀況(以人工智能人才、算力的流動分布為指標)和產品輸出狀況(以人工智能領域的論文、基準為指標)進行了數據化測度,指出:少數科技巨頭已經獲得了相比于高校、科研機構的絕對優勢地位,這在科技發展史上還是首次。比如,2004年人工智能相關專業博士生只有21%進入產業界,而這一數據到2020年已增長到70%。
大模型產業領域的“公-私”結構失衡,至少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嚴重問題:
(1)當前OpenAI和Google開發的大模型,雖然非常依賴海量的公共語料庫(包括但不限于維基百科、開源軟件、免費獲取書籍等),但是卻越來越封閉,很少生成新的公共產品;
(2)科技巨頭控制技術研發與擴散,將影響社會對前沿技術的獲取,進而不利于人工智能持續創新。
(三)大模型的多重社會影響逐步顯露,利益沖突加劇,面臨不確定性
近期,大模型技術在帶來一定收益的同時,也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而治理共識的缺失使得各類沖突頻頻涌現,使得相關的技術發展處于高度的不確定性狀態。
例如,2023年5月至10月,美國好萊塢爆發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編劇協會反對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來降低編劇的單位工資。盡管此次罷工以公司妥協(同意編劇協會要求,在三年內不降低編劇單位工資)為結束,但爭議的關鍵問題之一卻并未得到妥善解決:OpenAI等科技公司使用編劇劇本來訓練大模型,是否損害了編劇的版權并因此需要做出適當的賠償?
有評論指出,好萊塢編劇大罷工并非個例,實際上,不僅編劇協會,還有《紐約時報》、美國作家工會等也在2023年底陸續開始起訴OpenAI等科技巨頭。目前,法院對這類案子的態度尚不明確,但可以明顯看到,各個利益相關方與科技巨頭的分歧已經相當劇烈。

此前,美國編劇工會(WGA)在2024年7月開展罷工, 主要原因就是 AI對演員和編劇職業的威脅。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二、人工智能前沿領域的新探索
近期,國際科技產業界興起對于大模型技術路線的反思,并因此涌現出一系列的探索實踐和新理念,力圖擺脫“Scaling Law”面臨的發展困境。
第一類新探索:仍然堅持“Scaling Law”的有效性,但對這項定律做出重要調整。
典型代表是OpenAI于2024年9月發布的o1 model雛形。正如OpenAI指出的,o1 model是其探索不同于GPT技術路線的新嘗試,最重要的差別便是實現“推理時計算”而非“預訓練時計算”。
具體來說,o1 model將一個大問題拆分為一系列小問題(即形成推理鏈條,chain-of-thought),并允許模型在不重新訓練的情況下,通過推理時的額外計算來提高性能。這種新的路線更強調對人類推理性認知方式的模擬,能夠解決現在的人工智能不能維持答案的一致性以及不能實現長期目標規劃等問題。o1 model并沒有完全放棄“Scaling Law”。
也就是說,同樣還是依賴海量數據、網絡、時間和算力進行預訓練,但是在此基礎上,o1 model還增加了“推理”的數據、時間和算力,因此可以說是形成了一個大模型的升級版。也正是因為有了o1 model這樣的新探索,微軟CEO認為,“Scaling Law”并沒有達到瓶頸,而是可能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出現。

OpenAI首席執行員阿爾特曼(Sam Altman)近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面對DeepSeek的開源模型的挑戰,OpenAI必須要考慮制定不同的開源策略。
第二類新探索:部分接受“Scaling Law”可能失效的判斷,轉而綜合多條技術路線的優勢,對沖Scaling Law邊際效用減弱的不足。
典型案例是谷歌Deep mind的AlphaGeometry。眾所周知,人工智能發展史上長期存在著符號主義與聯結主義這兩條對立的技術路線,但符號學派早在1980年代末期就已經沒有了影響力,而AlphaGeometry是將符號模型與大語言模型進行了結合,在科技原理上找到了兩條對立的技術路線的結合點。
AlphaGeometry的創新性在于,它基于推理數據庫創造出大量合成數據,并基于合成數據的預訓練來找到輔助線構建的模式與規律,以此構成針對Scaling Law的修正。從實際效果上看,AlphaGeometry提升了歐式幾何題目(平面幾何)機器證明的效果(如IMO30道題目中做對25道),且通過計算實現了添加輔助線的推理能力,從而使證明過程可解釋。
第三類新探索:完全放棄“Scaling Law”,對深度學習等當前AI主流技術路線進行根本改變,以探索新的技術可能性。
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是杰弗里·辛頓提出的“非永生計算機”理念(改變當前軟硬件分離的“永生計算機”設計)。 辛頓指出,傳統的“永生計算機”是以計算機硬件與程序軟件相分離為前提,程序(包括權重和網絡)包含了所有的訓練知識,而這些知識與硬件無關,因此硬件可以支撐不同的程序軟件進行運行(也就是實現了計算機的“永生”)。
但是,辛頓分析認為,這種“永生計算機”的設計,無法解決目前需要消耗巨量能源來進行深度學習的問題,由此需要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改變傳統計算機結構。權重或網絡的調整不僅在程序層面,而且可以通過采用一種“前向-前向算法”(Forward-Forward Algorithm,FF算法)的新神經網絡學習方法,更好地解釋大腦的皮層學習,并且可以在極低的功耗下模擬硬件,從而使這種調整延伸至硬件層面,顛覆傳統的軟硬件分離的計算機形態。也就是說,計算機結構會隨著學習過程而改變,并隨著學習的變化或演進或結束(因此,計算機不再是“永生”的)。辛頓提出,非永生計算機可能是解決大模型在當前需要消耗巨量能源問題的“唯一可能性”。

諾貝爾獎得主杰弗里·辛頓曾設想一種情況,即人工智能系統能夠編寫代碼修改自己的學習協議。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三、激勵人工智能技術變革的制度條件
上述新的技術變革還處在探索階段;但是,全球資本、科研和產業等各界已經被激發起新一輪熱情,由此展現出支持多樣探索的制度條件的獨特重要性。目前針對大模型發展困境而涌現的各種新探索和新理念,非但不會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先位置造成威脅;相反,正是美國支持多樣探索的制度環境,使得科技產業界的持續創新只會不斷鞏固和加強美國的領先地位。
(一)開放的制度環境,是美國始終保持科技領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在開放的制度環境下,“Scaling Law”展現出來的種種問題都會引起科技產業界的重視,并且針對這些問題形成有針對性的探索。比如,是否可能以合成數據來解決訓練語料被耗盡的問題,是否可能通過改變計算機軟硬件分離的結構來解決大規模運算耗能過大的問題,是否可能在先進芯片領域創造出新的替代性產品,等等。
目前,這些探索都還沒有形成結論,既不能確定大模型技術路線是否已經發展到了極限,“Scaling Law”的效力是否真的已經耗盡,也無法判斷哪一條技術路線可能成為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主流。 但不管怎樣,在開放的制度環境下,來自世界各國科技產業界的各種新理念和新嘗試,在美國都有得到檢驗的機會,由此形成的多技術路線之間的相互競爭、相互促進,維持了美國在科技前沿領域的活躍度和創造力。
(二)產業與科研的高度協同,是保障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推進前沿技術發展的基礎
在人工智能領域,所謂基礎科研與產業應用的界限十分模糊。科技巨頭目前擁有的基礎研究能力及產業轉化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學術界和政府機構,由此生產出的科技產品也更具有通用性和應用性,能夠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美國少數科技巨頭形成的高度集中化的產業狀況,雖然衍生出相當大的社會問題,但這些巨頭進行的自我技術迭代以及相互之間的競爭,卻是保障美國推進前沿技術發展的重要基礎。
重大的科技產業創新需要巨量資源的投入,而且,在科技探索階段,也無法僅僅依靠財政資金的投入。因此,如同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說過的那樣,沒有“寡頭之間的競爭”,就很難有在重大科技產業項目上的持續創新,即通過“創造性毀滅”保持領先地位。
(三)激勵廣泛的創新和競爭,是美國維持社會活力的重要保證
各類挑戰大模型技術路線的新探索和新理念,在美國的制度條件下都能得到一定的資助,這是美國開放性創新環境帶來的好處。聯邦和州政府的財政資助、各類風險投資基金、公益基金、社會基金、企業資金等,構成了極為豐富而靈活的科技產業發展支撐。
就目前而言,是否有可能從少數科技巨頭之外創造出新的技術路線,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是無論怎么說,資本對于各類新探索的關注,給了各種有創造力的嘗試接受市場檢驗的機會。
如李飛飛教授在2024年4月宣布首次創業成立World Labs公司(主攻不同于大語言模型的“大世界模型”),在7月的市場估值就突破了10億美元,9月即完成了2.3億美元的巨額融資,投資方既包括硅谷知名投資機構a16z、NEA,加拿大風投公司Radical Ventures,以及英偉達公司的風險投資部門等專業科技投資機構,也有許多AI領域知名專家創設的科技企業。在這些投資方中,甚至還有World Labs力圖挑戰的科技巨頭的身影。

根據相關報道,World Labs在成立短短4個月內便成長為估值超10億美元的獨角獸公司。圖為斯坦福大學著名人工智能教授李飛飛。圖源:新華社
概況地說,美國開放的創新制度環境,為人工智能前沿領域的不斷革新創造了條件。美國的人工智能科研和產業沒有停下腳步,反而是以更具創造力、更具探索性、更加能吸引巨量資源投入的姿態在突飛猛進。這種新的技術變革探索,不會撼動美國的領先位置,相反會不斷鞏固和加強其在世界前沿科技領域中的統治力。
在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后,宣布將大幅“松綁監管”、激勵硅谷AI研發、增加對外國的科技封鎖和遏制力度。這種趨勢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在當前,國際科技產業界對于科技和產業問題的敏感度、對于新技術路線的創新性思考,以及國際資本對各種新探索的趨之若鶩,都表明一種新的科技發展范式正在崛起。
我們需要推動體制機制變革,適應、建立并且用好這一新范式。如果不跟上新一輪技術變革的浪潮,就會很大程度上有被排擠在未來科技發展主流趨勢之外的危險。
四、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政策的問題分析
中國人工智能市場規模近年爆發式增長,核心產業規模、市場增長潛力以及科研領域的各項指標都已處于世界前列水平。近期更有爆火出圈的DeepSeek,在大幅度降低成本之后,依然能夠實現性能上接近OpenAI等科技巨頭推出的閉源大模型。
但是,毋庸諱言,與美國整體居于領先水平的人工智能產業相比,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創新性依然不強,在制度和政策層面方面,還存在許多可持續改善之處。最新的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全球活力工具》報告顯示,中國與美國之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差距正在拉大。
(一)“重監管”的慣性思維,不利于創建高度創新的環境
中國長期存在一種“重監管”的慣性思維,即:在相關領域的科技和產業沒有發展起來時,就急于出臺監管措施;之后又由于監管措施本身制定得過于粗疏,而經常不得不在事實上進行“變通適用”或者“有法不依”。據不完全統計,在大語言模型興起之后,僅在2023年9月至年底的四個月時間里,部委層面和各地政府就出臺了近30種監管舉措,涵蓋面涉及國家安全、科技倫理、個人隱私、數據保護、版權糾紛等。
然而,當時的中國大模型研發還處于“跟風”狀態,應用方面也剛剛開始有所探索,這些監管舉措擔心的問題還沒有真正出現,只是一種猜測或想象中的問題,因此我們看到,監管政策的表述通常是比較原則性的,沒有操作細節,即使當真出現了相應的侵權行為,也無法依靠這些匆忙出臺的舉措來進行處理。但是,這些表述嚴厲的政策文件,對于產業界產生的影響卻是真實的。
近年,許多大企業以及一批人工智能獨角獸企業都熱衷于啟動大模型“出海”,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海外的制度環境相對穩定,不會像中國政府這樣可以輕易對創新環境進行大動作的干預。
當然,這并不是說對于人工智能發展中潛藏的各種風險不要實施監管;而是需要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適合創新的監管”。2022年,有一位歐洲學者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著作,很有影響力。作者梳理了美國、中國、歐洲的數字技術監管規則,指出美國是“市場驅動型監管體制”,中國是“國家驅動型監管體制”,歐盟是“權利驅動型監管體制”。作者認為,根據各地不同的制度和文化條件,這三種監管都有其優點和缺點。這部著作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但是,我們認為作者沒有提供真正富有啟發性的見解。
實際上,“適合創新的監管”一定是尊重市場機制的,或者更直接地說,是“發展先行的監管”。歐盟國家在新一代高端科技領域沒有培育出有規模的企業,因此在規則制定過程中沒有產業界發出的聲音,相關的監管規定通常圍繞抽象的“權利”而展開,結果是更加嚴重地限制了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
在大語言模型興起之后,歐盟也出現了一些專門從事應用的企業,以相對小的參數量追求普及效果,如歐洲最大的私人人工智能實驗室Silo AI、法國的Mistral AI、德國的大模型企業代表Aleph Alpha等,在應用方面表現出發展潛力。但是,由于受到歐盟監管規則的制約,這些企業難以獲得較大發展,近期都面臨被美國大公司收購的情景。歐盟委員會2024年發布了研究報告《歐洲競爭力的未來》,提出在人工智能等多個新興技術領域追趕美國和中國。然而,現實中歐盟面臨諸多挑戰,如產業基礎薄弱,人才大量流向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國家,因此,歐盟能否在這些領域取得顯著進步,目前還難以確定。
美國的監管體系是圍繞著創新和競爭展開的。在很多案例中,發展與監管之間也經常出現表面看來難以緩和的矛盾,但是,監管機構通常偏重于激勵創新和競爭。比如訓練大模型的數據語料極為龐大,容易出現版權爭議問題,美國目前沒有確立統一的監管思路,大量關于“數據權屬”的討論也僅停留在學術研究中,沒有對監管政策和司法實踐形成影響。這種模糊的態度的確解決不了已經發生的社會利益沖突,但卻為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空間,而隨著利益爭執的日益顯著,美國法律體系中的彈性特征也會相應發生作用。
如2024年11月7日,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以“原告欠缺美國憲法第3條規定的訴訟資格”為理由,駁回了兩家公司針對OpenAI的版權侵權起訴。這是一個以“程序問題”為由的處理方式,既為法律界進一步探討如何應對相關問題留出了余地,又不至于阻斷其他企業或個人實施侵權訴訟的努力。
中國需要避免陷入歐盟的當前發展狀況,應當針對創新領域大力實施“去監管”的改革。
就新興產業發展來說,中國和美國領先歐洲太多了,如胡潤研究院近日發布的《2024全球獨角獸榜》(Global Unicorn Index 2024),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價值10億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其中,美國有703家,中國有340家,歐盟國家僅有109家,連英國都有53家,印度有67家。

據《2024全球獨角獸榜》,中國擁有全球1/4的獨角獸企業,主要來自人工智能、半導體和新能源產業。
但是,中美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另一家專業調查機構的報告指出,美國在通用人工智能(AGI)領域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誕生了如xAI、OpenAI等14家大模型相關的獨角獸企業,推出了包括AlphaGo、ChatGPT系列等重大技術成果。其中,估值最高的OpenAI,其估值達到了驚人的29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三大獨角獸企業。而中國的生成式AI和大模型相關的獨角獸企業共有8家,其中估值最高的企業目前估值約30億美元,且成立時間僅一年左右。
特朗普“新政”的理念是對內增強創新激勵,對外增大封鎖和遏制,如果我們不創建更為開放的創新環境,有可能“逼迫”我們培育的獨角獸及其他優質企業紛紛赴美發展,導致我們與美國的差距越拉越大。
(二)政策協同性不強,改變不了科研與產業“兩張皮”狀況
我國的科技發展理念上長期存在一個誤區:以“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轉化”的線性思維來看待科技創新活動,人為地割裂了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與產業發展之間的有機聯系。在人工智能領域,線性創新思維的危害更為嚴重,因為人工智能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
其實,我國早在2017年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就已經提出“堅持人工智能研發攻關、產品應用和產業培育‘三位一體’推進”的部署。2017年11月,科技部、發改委等15個部委組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推進辦公室,并推出了“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計劃。
2022年7月29日,科技部等六部門印發了《關于加快場景創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但是,在推進的過程中,由于各個配套性政策相互之間缺乏足夠的協同性,既不能克服各部門各自為政的頑疾,又難以深度融入多樣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產學研之間的阻遏依然難以打通,科研與產業仍是“兩張皮”。
例如,截至2024年,已批準建立了23家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但這些平臺多依托百度、阿里云、騰訊、科大訊飛等頭部領軍企業建設,仍然是按照線性思維加以推進,研究成果的轉化成本極高,對廣大區域和廣大行業的具體發展難以形成顯著幫助。而且,在該計劃的推進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抓手和引導,雖然平臺定位為加快人工智能應用創新,然而卻不能推動上下游產業的聯合,尤其無法與高校等科研機構建立聯動。
而在基礎研究方面,2018年4月教育部印發了《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清華、北大等幾十所重點院校相繼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時,國家在一些條件優異的城市部署了專門負責人工智能基礎研究的國家實驗室。但是,經過數年的運作,除了少數幾家機構能夠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與當地領軍企業建立合作關系之外,大部分研究機構與產業發展是脫節的,科研成果得不到接受市場檢驗的機會,從而無法對行業產生影響力。
(三)對多元探索激勵不足,難以形成不斷推陳出新的生態
目前,就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和研發資源分布而言,在區域層面,我國呈現出明顯的東強西弱態勢。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研究中心2023年發布的《中國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圖研究報告》顯示,西部地區除成渝經濟區與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并列為人工智能算力四大領先發展核心區域外,其他城市區域全面落后于東部領先地區。

根據《中國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圖研究報告》,北京、廣東、浙江、上海等地的大模型數量最多。圖為全國范圍內的算力基礎設施分布情況。
經濟發達區域更容易吸引科技資源的涌入和培育新的科技資源,這是客觀事實,但是,公共政策需要打破線性創新思維,采取一些激勵措施來引導科技資源基于各地的發展需求探索新的科研方向。
實際上,美國聯邦層面已經在實施這樣的激勵措施。2019年10月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統籌,聯合多個部門發起了美國國家人工智能研究院(NAIRI)項目,在美國五大區域各布局科研資源,研究方法專門強調“基礎研究與應用啟發性研究一體推進”,研究領域涵蓋了多樣應用需求:不僅有發達地區領先的大數據、機器學習、算法優化等應用方向,還包括了農業、教育、網絡基礎設施等在欠發達地區有廣泛應用的領域。
到2024年,NAIRI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一個由100余家資助組織、500多個受資助機構和合作機構、約700余名專家參與其中的合作網絡,形成了美國最大的人工智能合作生態系統。
我國還沒有形成健全的激勵多元創新探索的制度機制。
第一,創新的資助渠道仍然相對單一。國家的大量科研經費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系統,多數成果對經濟社會實際發展沒有產生直接作用。在人工智能發展領域,除上海、杭州、武漢、廣州、深圳等少數城市有政府參與發起和支持運營的人工智能研究院之外,絕大多數地方并沒有針對人工智能研發機構的組建制定明確的規劃和提供經費支持;
第二,研發主體同樣相對單一,產業界缺乏創新性的基礎支撐。中國的人工智能相關專業人才過于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這些系統目前的考評措施和激勵機制,較難引導大量人才投身于支撐產業發展的科研工作。
近年,在大語言模型崛起之后,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涌入這個單一的賽道,形成“百模大戰”的浮躁場面,正說明了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多數缺少創新性科研。據統計,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一年時間內,中國就發布了238個大語言模型,相當多產品性能雷同。DeepSeek-V3的橫空出世,一度讓媒體驚嘆,但是DeepSeek-V3更大的成就是實現了多原理和多技術集成,可以算作工程學意義上的創新,還沒有形成引領原創性探索的效果。
五、開放的創新環境的特殊重要性
美國近年吸引了大量中國AI科技人才赴美工作,進一步加劇了中國人才的流失。有統計顯示,在過去10年里參加 NeurIPS大會(神經信息處理系統大會,是機器學習和計算神經科學領域的國際頂級學術會議)的2800名中國AI人才當中,約有75%目前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工作,也就是說,有2000名左右的AI人才已經離開中國,其中大約有 1700人(在流失人員中占比85%)人去了美國。
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后,會在其國內實施“松綁監管”,加速硅谷的AI研發,同時任命對華持強硬立場的人士出任科技、產業和能源等決策部門的主管。當前,中國最需要防范的就是美國通過內部改革,更大力度地吸引全球資本和科技產業資源涌入,造成中國科技人才和企業的大量流失。
此外,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遏制政策也在不斷增強力度,特別是對半導體、芯片、AI算法等核心技術的封鎖,使得中國在機器人核心技術的突破面臨巨大挑戰。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德國、日本、韓國等制造業強國,也在大力推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機器人技術的研發,直接影響著全球市場的分配。
面對這種緊迫的壓力,中國如果不大力構建開放的創新環境,推動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的開放創新、自主研發和產業化,未來可能會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不利地位。這里尤其需要強調“開放”對于構建良好的創新環境的重要性。
(一)只有“開放”才能科技“自立自強”
人工智能領域日益增強的技術變革趨勢,要求我們構建更加開放的制度政策環境加以應對。而特朗普上臺所倡議的對內加強創新激勵、對外加強科技遏制,同樣要求我們在開放的創新環境中積極進取。事實上,“開放”是真正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基本制度條件,“開放”也是沖破科技封鎖和遏制的唯一手段。
需要指出,正是由于美國的遏制政策,導致我們國內出現了一股逆反情緒,把“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曲解為“關起門來做科研”。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
第一,“關起門來做科研”是做不出對經濟社會長遠發展有用的自主性科研的。
我們不從理論上來論述“思想市場對于科技進步的重要意義”等等基本院長,僅例舉一個事實。 2023年初,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俄羅斯高級記者季莫費·尤里耶維奇·斯科連科的著作《蘇聯發明史:從1917年到1991年》中譯本,梳理了許多蘇聯取得的基礎研究領域以及高新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這些在封閉狀態下實現的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與外部世界完全脫鉤,與國內的生產實踐也完全脫節,最終只能被束之高閣,形成不了“自立自強”的態勢。
眼下,由人工智能激發起的新型科技發展范式,已經不允許在封閉環境下從事科研和產業發展了,全球的資本、數據、人才、科研和工程力量都被吸引到這些新產品、新理念、新技術變革探索周圍,不去適應、建立并且利用好這個新的科技發展范式,就有被排擠出世界主流科技發展潮流之外的危險。
第二,只要我們不自己主動地關起門來,他人的遏制政策也起不到把我們封鎖住的效果。
有很多細節證明了目前全球資本、科技、產業存在著復雜的關聯性。比如,有消息人士指出,在美國聯邦政府最近公布的新一輪芯片出口管制名單中,中國的長鑫存儲等企業沒有被列入,部分原因就是這些企業的主要供應商是亞洲最大半導體設備制造商之一東京電子,這家跨國企業通過它在華盛頓的商業伙伴影響了白宮的決策。
美國對華持強硬立場的政客們自然也能認識到全球利益關系網的復雜性,所以在近年不斷推動政策,要把臺積電等先進制造類企業引入美國本土,以便為實施更嚴厲的科技遏制舉措做準備。然而,要引入這些企業需要投入巨量的資金,而且這些先進制造、科技類企業對于從業人員的技能要求相對較高,不會直接給一般選民創造就業機會,因此,諸如此類“為進一步遏制”而不計成本實施的舉措,都有可能在美國國內引發沖突、加劇美國社會的分裂,通常不易落地。
所以,這一點必須得到反復強調:加大開放力度,才是應對當前內外發展環境劇變的唯一正確選擇。我們的主張并不是反對“科技自立自強”,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只有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加大對內對外的開放程度,才能真正在各方面實現“自立自強”。
(二)必須加大對內對外的開放力度
當前,中國最需要防范的,是美國通過內部“松綁監管”來更大力度地吸引全球資本和科技產業資源流入。中國需要大幅實施制度創新,充分激發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成渝經濟圈等等區域在科技資源、產業基礎、經濟實力方面的優勢潛力,以創建新時期的“經濟特區”的舉措來保障開放性,動員海內外資源,打造人工智能創新發展高地。
第一,支持各地既用好已有的優惠政策,又積極對接各類國際新興規則。
一方面明確形成“國家政策已經規定的內容,地方可以直接進行適用”的支持性舉措,另一方面推動各個區域借助中央的政策賦能,積極對接國際新興自由貿易規則和金融規則,以及《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最新國際協議的開放性規定,吸引海內外創新型企業、人工智能獨角獸企業落地,創建人工智能全球優質資源聚集區。
同時,大力探索新型監管規則,如放松互聯網“防火墻”等監管措施,激勵開源社區等第三方基于全球的可用數據,獨立建立公共數據語料庫,支持各類人工智能企業借助公共數據語料庫進行模型訓練,并且探索應用方案。
第二,創新財政資金的使用方法,形成以財政資金的投入為引擎,鏈接社會資金共同投入的多元資助格局。
通過稅收優惠、獎補等多項舉措支持各類資本投入人工智能科研、產業化發展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同時,鼓勵各類資金圍繞產業發展需要,建設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臺,提供數據共享、模型訓練、測試驗證等服務,降低企業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門檻。此外,設立專項激勵措施,鼓勵企業和科研機構合作建設面向全社會開放的AI計算平臺,為各行業提供計算資源支持。
第三,大力發展中介機制,加強科研機構對接市場的能力。
一是發展“商業中介”助力市場對接。 支持商業咨詢、市場調研、品牌策劃類商業中介機構與人工智能企業合作,對于促成企業重大合作、市場拓展項目的商業中介給予獎勵,促使中介機構積極為企業挖掘市場機會,讓科研團隊專注于技術研發;
二是鼓勵青年學生從事“科技中介”業務。提供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激勵政策,支持懂技術的青年學生創辦專業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鏈接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實驗室、研究院所等等,推動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在各行業的落地。
第四,建立“全鏈條培育人才”的創新性人才政策。
打破按照學歷、學位、履職經歷等標準實施人才招聘、發放人才獎補的方式,突出跨專業性、協同性和實用效應。一方面,通過事前支持創業創新、事后進行績效獎勵的方法,鼓勵各類優秀人才干實事、出佳績。
另一方面,聯合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業,廣泛建立先進技術培訓平臺,并且建立獎補政策,鼓勵各行各業的青年人積極學習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知識,將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與各行各業既有知識相結合,推動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產品在千行百業中應用。
第五,建立健全科技幫扶機制,帶動欠發達地區共同發展。
一是建立科技幫扶結對。推行“強企+弱企”結對幫扶模式,組織人工智能龍頭企業與欠發達地區相關中小企業一對一幫扶。政府對幫扶成效顯著的龍頭企業,在稅收減免、項目申報優先度上予以傾斜。對被幫扶企業,給予免費技術培訓、設備補貼等支持;
二是加強對欠發達地區的科技人才培養。支持發達地區的科研團隊深入欠發達地區開展技術培訓與合作,培育人工智能專業與具體行業領域交叉的復合型人才;
三是鼓勵科研機構與企業合作,共同建設研發中心,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欠發達各行業的普及與應用,尤其是在制造業和農業等行業中,幫助當地提升整體技術水平,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本文得到鄭永年教授的悉心指導,同時得到華南理工大學多位專家學者的指導和幫助,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在讀博士生劉金程對本文亦有貢獻,特此感謝!
*本文作者:
賈開,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長聘副教授、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點擊圖片閱讀更多賈開的文章)????
蔣余浩,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點擊圖片閱讀更多蔣余浩的文章)
戴明潔,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點擊圖片閱讀更多戴明潔的文章)
張弦,中國移動研究院中移智庫管理與運營中心研究員、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鄭永年:中國能否成為一個“開源國家”?
鄭永年×黃鎧×袁曉輝×劉磊×劉少山:人工智能社會的機遇與挑戰
蔣余浩:中國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路徑研究——基于“非線性創新觀”的探索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廣東
廣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