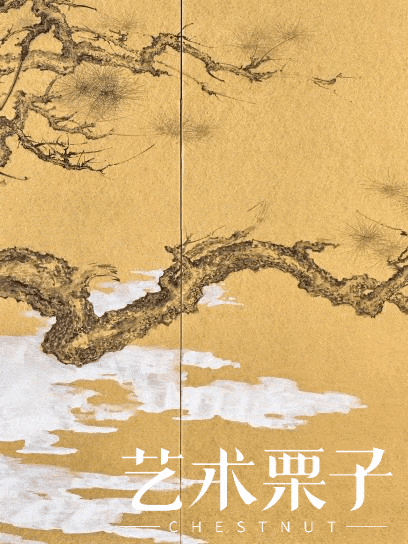
如何在這個不安的世界里,尋得安靜的一隅,這是頌的初心,也是萬亨所篤信的藝術路徑:君子之道,詩意的自然主義。
——策展人蘇芒
在“50-90:龍美術館十周年特展”這場如同星河般璀璨的近600件藝術瑰寶中,匯集了50后至90后五代藝術家的匠心獨運,其規模之宏大,堪稱史無前例。主展廳穹頂之巔,萬亨的畫作熠熠生輝。萬亨,這位在我國南方嶄露頭角的青年水墨藝術家,早以“中國屏畫青年領袖”之譽享譽畫壇。
2022年由龍美術館館長王薇精心策展,萬亨于上海龍美術館呈現個展“涵墨鏤金——萬亨屏畫展”;2024年由頌藝術中心館長蘇芒親自策展,個展“君子”在北京展出。一南一北的個展,讓大家對青年藝術家十分好奇:是誰憑借扎實的水墨功底,在宋代院體畫中借古開今,躋身當代藝術并占有一席之地?

2002年萬亨(右)與王薇(中)

2024年萬亨(左)與蘇芒
萬亨出生于浙江溫州平陽一個叫做萬全的地方,兒時記憶中祖父常被鄰里間求去寫書法,童年的他在爺爺的書房與筆墨為伴長大。小學時,在別人畫阿童木亂涂鴉的年紀,他已經開始喜歡毛筆作畫的感覺。高中時曾去杭州拜師學畫,后考入中國美術學院。在浩如煙海的中國畫世界里,他最神往的是宋代院體畫,是宋徽宗。那些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的美學氣度,讓他自此沉迷于對宋代院體畫的研究和繼承。
2022年是萬亨創作的轉折之年,臨近四十不惑之時,確立了屬于自己的藝術語言和表達。松的主題、金箔屏風的形式、扎實的繪畫功底、獨特的觀看視角,共同構成他的“標識”。之后僅僅兩年時間,可以看到藝術家在確定方向后,創作上的突飛猛進,而將西方構成融入中國水墨,萬亨逐漸有了自己的方法。



萬亨個展“君子”
2024.11.2-12.16 頌藝術中心
萬亨的松是特別的。去掉龐雜的自然背景,在實體松的基礎上,加入更多內心的想象,完成從自然之松到心象之松的轉變——以物抵心。自此,他開始有了鮮明的個性化特征:與古人精神遙相呼應的東方主義美學、金色屏風與墨色古松的視覺沖擊、真性情的兼工帶寫的筆墨意趣、突破傳統制式的當代形式、簡潔雅致的色彩及畫面構成……
近兩年,他以個人化的藝術風格,作品中加入更多西方構成方式,為中國水墨的呈現注入更多觀看的空間維度。《游龍》中以石綠繪就的傳統中國畫中不存在的豎線、《武陵仙枝》中以白創作的類似油畫肌理、《歲寒》中以色塊重新構建的平面空間關系……他的作品,始終扎根于傳統中國畫媒材、語言的當代融合,不以形式為桎梏,打破了中西方的次元壁壘,從創作到觀看,成為一種求新圖變的新法門。

萬亨《游龍》 紙本灑金 59x88cm 2023

萬亨《游龍》局部

萬亨《歲寒》 絹本設色 103x93.5cm 2024
師法自然,尋山訪松,萬亨舍棄古人程式化的觀看及構成法則,遵循內心的一種真誠,全身心地去體驗自然中真實的古松。尋覓古松在與自然抗爭中的一種蒼勁、野性的生命力,以及真實美感下所賦予的高士氣節。
與松為友,始終把第一種感覺落在筆端。幽遠虛極、直抒胸臆,他進一步強化心中的松,使得金色屏風與墨色古松相得益彰,凸顯一種詩意化的氣息和精神內涵,將兩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自此,萬亨也有了更為清晰的一個藝術線索和方向。

萬亨《武陵仙枝》 金箔屏風 110x260cm 2024

萬亨《武陵仙枝》局部
抵達這一路徑,萬亨走了30余年。扎根于強大的中國繪畫系統,在西方當代的圍攻之下,建立自己的方式,這是以中國水墨為主體的藝術家的共同課題。這個問題也困擾了萬亨很久。當松漸漸成為創作的母題后,這條路突然就通了。
藝術生涯早期的15年時間里,他更注重對于古典技法材料學的理解和積累,深入古典文學以及傳統文化精神等,以此反思東方傳統的國畫藝術。最近幾年,萬亨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不僅涉及中亞、波斯、印度、日本等雕塑、繪畫、壁畫,還有西方現當代的作品,比如克林姆特、羅斯科、康定斯基、培根等。正是基于兩類養分的交互作用,無論是色彩上,還是空間的線條上,都直接激發了新作的呈現。


萬亨在工作室
創作上的研究,進一步激發了藝術家創作思路和生活方式的開放性。收藏古董與近現代書畫,也收藏當代藝術;喜歡盆景,也喜歡當代的工藝作品;習慣吃中餐,對西餐也來者不拒。作品形式上,從傳統的平面到立體的屏風,激活的不僅是樣式,更是追尋詩意化的東方主義美學話語,踐行個人化的君子之道的藝術實踐。
形式為表,卻依然可以對內容產生影響。文震亨在《長物志》中提及“屏風之制最古”。屏風以頗具朦朧美的東方美學,營造著中國文人含蓄與內斂的空間意境。萬亨賦予了屏風新的藝術觀念,把這一古老的藝術以新的形式與內涵,再度拉入我們眼簾。以屏風形式為基礎,材料上選擇古絹、金箔,重構了屏風在物理空間的多維式張力,以期穿梭時空與古人對話。

萬亨個展“君子”
2024.11.2-12.16 頌藝術中心

形式的開放性,也開啟了一種新的工作方法。萬亨讓朋友隨意做了100個畫框,畫框的形式由制作者自行決定,因此有了此次展覽中形態各異,甚至有些奇特的“珍禽集”系列畫框。他的創作基于那一刻看到畫框的感覺,而非原定計劃。
依據西方肖像法則,構圖上突出珍禽形象的主體性,就這樣,他以好玩的心態創造了屬于他的當代藝術新形式。恰如他對《藝術栗子》所說“花鳥只是畫大畫的一種調劑”,其中的松弛和自如正是這些作品的珍貴之處。



萬亨工作室
為了松,萬亨在工作室養了上百盆的松類植物盆景;為了珍禽花鳥,他養過50多只不同種類的鳥,深入觀察。如此生動的萬亨,保留了一種當下難能可貴的藝術家應有的學術品質,追求極致的他足以讓我們感動并記憶深刻。
或許正是基于細膩的生命體驗,才有了充滿活力的筆墨意趣,生機盎然的畫面彰顯出了真性情,使他得以脫離宋人繪畫刻板之弊。在探尋作品與時代的緊密關系中,逐漸找到自己的一條深入踐行的藝術路徑。
Q&A
栗子對話

萬亨
藝術家
從“松”開始
藝術栗子:松是最具中國文人代表性的物象,對您的特殊意義是什么?與古代對松的表意相比較,在當下您想通過松,來表達和解決什么問題?
萬亨:松和傳統的四君子、歲寒三友是一樣的,也是東方文人士大夫精神的一個外化的主體。對我而言,我想表達的還是對古代文人士大夫精神的當代回響。松是讓我與古代先賢們嫁接聯通的一個物象,希望通過畫面,在精神上去追求自己對于文人高士的一種情懷契合。

萬亨《君子》 金箔屏風 150x150cm 2024

萬亨《凌云》 絹本設色 73x82cm 2024
藝術栗子:您以畫松揚名藝術界,什么樣貌的松會特別吸引您?若把松比作人,如何形容您筆下松的狀態?
萬亨:在繪畫上,自然界的松的造型和我心中理解的美感造型,其實還是有區別的。我們要尊重物象本身的生長規律及特點,如同養盆景一樣,是人和自然在對話關系下的一種引導。這不是簡單的藝術家復制性拷貝到畫面的表現對象。
有一定歲月沉淀和歷史感的古松會更吸引我,他們的姿態會更加滄桑和遒勁,以頑強的生命力去對抗自然惡劣的環境,其所傳達出的力量感恰恰能打動我,生長的美感更會給我心靈上的啟發。
如果把松比作人,我傾向于與我對應的歷史當中的一種高士的形象,有獨立的性格,不懼自然惡劣環境,生命去綻放的那種狀態。


藝術栗子:為什么去自然中訪松,您都去過哪些地方?如何選擇采風地點?
萬亨:首先去游歷山川感悟自然,這能夠觸發我內心對于繪畫的表達欲望,以及追慕古代畫家的情懷;其次在游歷的過程中,能夠看到在書齋或者是畫冊之外的很多東西。書籍和畫冊都是被別人提煉、加工過的內容,不是第一手素材。從自然中得到最新鮮的一手資料和素材,對我的養分也是最足的,也是最能夠提煉出自己喜好的行為方式。
我每年會有一些時間去游歷,但沒有特定規劃。江浙一帶的天臺山、雁蕩山、黃山、華北的太行山,川西青海、陜西山西的一些野外荒山我都會去。名山大川的樹未必就一定好看,可能一個無人問津的小村莊的一棵古松,在行程方便的情況下,我也會去體會和觀察。


萬亨在訪松路上
藝術栗子:在采風畫松的工作方法上,從自己帶著攝影器材拍攝,轉變到組織團隊高清拍攝,這是為什么呢?
萬亨:尋山訪松是一個藝術游歷過程,我在現場更多的還是以感受和觀察為主。回到工作室,借助一定的影像和圖像資料,進行反觀和回望,可以產生對當時創作點的重新激發。自然環境對創作其實是有時空性的,對我而言,在工作室的創作會和現場創作幾乎是一個平行狀態。自然界的松雖然看著很美,但我在創作中需要二次加工和處理,畫面上的松與自然中的松的形態的吻合概率并不高。

萬亨《孤秀》 絹本設色 58x38cm 2024
藝術栗子:自然的松—心中的松—筆下的松,這個意象轉變中,您是怎么看待自然與松,松與人的內在關系和關聯?
萬亨:我覺得這三者在藝術表達的時候,不是那么孤立的。我去思考的那一刻已經經過藝術融合。自然的松呈現的是外化的物象,這其實是形的概念;心中的松,經過一定的思考和藝術處理,呈現出的是帶有精神和意涵的形象;筆下的松,恰恰是把這種形象表現出來,讓畫面與觀者產生新的關系,尋找精神上的共鳴。于我而言,這是我和觀者對話的橋梁和媒介,在此刻能產生一定的碰撞。
不止于形
藝術栗子:在您的系列屏風作品中,在空間及作品本身的氛圍營造上,您更多是出于什么考量?
萬亨:我選擇題材研究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個人喜好,屏風對我個人而言,只是一種材料和媒介,或者說一種載體。通常在美術館里,我們見到的傳統國畫大多是中小尺幅,而屏風本身具有一個大畫幅的尺度,以及整體金色的視覺沖擊力,無論從畫面內容的影響上,以及對空間環境氛圍的渲染上,我認為是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視覺震撼力。
屏風本身的條狀呈現方式所形成的秩序感,具備了一種當代繪畫的藝術語言,產生具有當代繪畫審美視覺的美感。我覺得這兩者并置,會讓古典又具備一定的當代性。重新按照一個并列組合的方式呈現,這是我想要去做的。

萬亨《大夫枝》 金箔屏風 110x260cm 2024
藝術栗子:屏風和金箔象征地位,松則是高士,在畫境上怎么處理奢華貴氣與致虛極、守靜篤之間的平衡?
萬亨:之前有零散的創作,2019年起集中以屏風進行創作表達。在金色屏風上,我基本是以水墨為主,以墨色去呈現一種墨的沉淀感。單一的墨色的穿透性會更強,會讓畫面在金的顏色干擾上,不至于顯得那么繽紛華麗。墨跟金色不僅融合度好,墨色的深和金箔的亮會形成一種視覺對比,我有意以偏深重的墨色來降低金色的視覺暴力感,把它往沉穩的方向壓下去。出于這種考量,畫面當中有時會用一點點的色彩,比如石綠、白,起到點睛的作用。


萬亨個展“君子”
2024.11.2-12.16 頌藝術中心
藝術栗子:在珍禽作品中突出物象的主體關系,畫面構成方式頗有現代性。在不斷加減的過程中,您個人的創作心路是什么?
萬亨:我并沒有按照傳統繪畫體系的構圖法則和評判標準,來思考創作的問題。我是按照肖像的繪畫方式,更加突出物象在畫面中的主體性,視覺上傳遞沖擊感,以三角比例的平衡關系構建穩定性。通過色塊的形式處理,形成更加嚴謹的規范和視覺的集中點。以歸納和概括再次強化這層關系,讓它更具有一種畫面的集中和核心的規律感。同時,增加背景中同色系的不同色塊對比,形成新的視覺元素。
中得心源
藝術栗子:宋人院體畫對您的最大影響是什么?在哪個階段開始了宋畫研究?
萬亨:對宋代院體畫的研究是我在中國美術學院讀本科時期,那是一個必經的學習過程,從工筆慢慢地往小寫意再到大寫意。我個人對偏工細類、造型嚴謹的畫面是發自內心的喜歡。宋代繪畫中,宋人的這種嚴謹度,包括追求的極致、精準的筆墨表現,這些和我個人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會略微多花一些工夫去積累、臨摹和學習宋畫體系。

萬亨《支離叟》 紙本灑金 59x88cm 2024
藝術栗子:東方精神是一個探討了百年的話題。當下,您如何理解東方性和東方精神?
萬亨:東方性和東方精神是從小所吸收和學習的文化思想,刻在骨子里的東方意境磨滅不了,文化思想會覺醒,東方性是自然心性的一種流淌和書寫。我覺得不需要刻意去討論東方精神,在時間軸線中,隨著社會發展以及精神文化的發展,這自然而然會在作品中落下烙印。30年或者50年之后回望,其演變就是自然的生命軌跡。


萬亨個展“君子”
2024.11.2-12.16 頌藝術中心
藝術栗子:您的作品方向對您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影響?會使您選擇古意古人的生活嗎?
萬亨:摹古一定不是一種刻意追求,只有當精神生活有需要時,自然而然就會去攝取這方面的營養。當代科技以及工業化的進步,帶給我們更多生活上的便捷,我們回不到和古人一樣的狀態,而且也沒有必要回到一樣的狀態。然而,古人的某些精神性追求,恰恰在當下就是缺失的。我會去彌補這部分內容,在古和今之間擇優和擇需而選,為我所用。

文字|李蕊
圖片|頌藝術中心、萬亨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北京
北京








































































